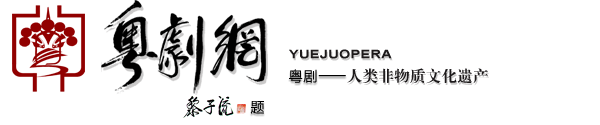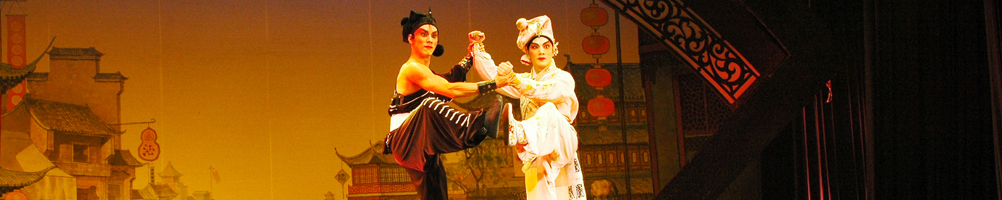是忠是庸 删绪增翠——我改编《史可法沉江》的一些思考
发布时间:2025-01-17 作者:李悦强 来源:粤剧网 点击:
2024年6月9日,肇庆市国家二级导演杨树光夫妇带肇庆市粤剧团文武生梁恒风来平洲见我,委托我改编昆曲《桃花扇》中“沉江”一折,要求时长约15分钟。我接受了委托,着手将其改编为粤剧折子戏《史可法沉江》。

昆曲《桃花扇·沉江》故事并不复杂,剧情是这样的:明朝末年,清兵南渡。史可法率三千子弟兵迎战,奈何寡不敌众,子弟兵壮烈殉国。史可法闻南京被围,与老马夫奋勇杀出扬州,意图力挽国难。岂料行至长江岸边,得遇故交龙友,得知主逃国破、兵降官散,可法一家老小俱丧在清军刀下。至此,遗臣相对,老马夫以史可法为榜样,弃母存忠。史可法忠心无寄,自责是亡国罪臣,沉江就义。剧情虽然简单,但问题随之即来。
关于史可法在南明的作用及他的死,在史学家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和享誉史界的明清史专家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均有颇为详尽的记述,撷其要者言之:“史可法殉难扬州的具体情况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但为清军俘杀则无疑问。”这就明确了一点,史可法是被清军俘杀,不是沉江死的。
此外,顾诚还认为,“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明史》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
这样说来,如果从大处着眼,史可法并不值得歌颂。
对上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不得不去做一番思考:史可法是被清兵俘杀的,那么,孔尚任这本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为什么写史可法沉江呢?我揣摩有以下四点:
(一)孔尚任是编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戏字半边虚,编剧有虚构的权利。
(二)编剧也不能空穴来风、凭空臆造。孔尚任自言,此剧“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孔尚任于公元1686年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到1689年的冬天才回北京。这时期他结识了明末遗民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及僧人石涛等。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孔尚任对南明亡国的感慨,也丰富了《桃花扇》传奇的素材。至于他如何从这些生活经历中提炼概括出“沉江”一折,那就要问孔尚任了。
(三)清朝有两项大政是明显的,一是安抚民心,二是文字狱,可称双管齐下。那么孔尚任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桃花扇》传奇,特别是“沉江”一折呢!我以为孔尚任不写史可法被俘杀而写沉江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是孔尚任大文豪聪明之举。因史可法在清朝统治阶级中有一定位置,乾隆皇帝还御批在扬州梅花岭上建立史可法纪念馆呢!再者,如果明写史可法被清兵俘杀、随之而来的情景就是“扬州十日”,清军因史可法顽抗怒杀八十万扬州百姓。我想,这是清朝定鼎后不想再提的血腥史。孔尚任写史可法“沉江”就回避了这一段清人有意掩盖的史实,也逃脱了文字狱的羁缠。所以,尽管《桃花扇》传奇写了“兴亡之感”,清廷也没有明治孔尚任反清之罪,只是到了《桃花扇》传奇演出之后的第二年春天,孔尚任才因一件疑案被罢官。对此,王季思教授说:“根据马雍先生的意见,认为这‘很可能和《桃花扇》的脱稿有关’。”(见1954年5月24日《光明日报》上马雍先生所撰《孔尚任及其桃花扇》一文)
(四)孔尚任写史可法“沉江”还有一层意思,他不是说要“写兴亡之感”吗?民谚云“栋梁折,大厦塌”。在孔尚任的眼中,也可以改为“栋梁折,南明灭”。写了史可法沉江,就必然显示了南明的覆灭。后来虽有打着“复明”旗号的义军,但已经不是国之劲旅了。这个“亡”字就落实了。
以上就是我对史可法之死的写法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对史可法功过的评价以及史可法是否值得歌颂?
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可法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引下,我们不妨看看另一种观点及评价。先看看这个南明王朝,夏完淳《续幸存录》说:“朝廷与外镇不和、朝廷与朝廷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冠之事,置之蔑闻。”这就是南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再看看王季思教授如何评价史可法吧:“当时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比较贤明的人物并不是没有,传奇中所写的史可法就是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统治集团走向腐朽、没落,他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陷于孤立。《桃花扇》传奇演南明王朝建立之后,史可法即因为马士英所忌,出守江北。到他镇守扬州之后,江北四镇将士又因早就与马士英勾结、不听他的指挥。明末清初有些史书作者也看到了史可法才能短绌的一面,然而重要的不是史可法个人才能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形势使史可法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挥的问题。传奇第十八出当四镇将士为争夺扬州自相水火时,史可法只能写一张告示来调停,效果当然不大的。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部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一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
“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
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他的《中国史》(原名《白话本国史》)中有专门章节谈福唐桂三王的灭亡,篇中略摘:“朝廷之上,纷纷扰扰,而福王又昏愚无比,当这国亡家破的时候,还是修宫室,选淑女,传著名的戏子进去唱戏;军国大事,一概置诸不理;明朝的局势,就无可挽回了。……史可法又回到扬州;则清兵已入盱眙。可法檄调诸镇来救,可没有一个人来的。可法力战七昼夜,扬州陷,可法死之。”
从上述的引文来看,把南明的覆灭归咎于史可法的施政不当而没有从南明整个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及其走向没落的必然性来全面分析,只指责史可法某些弱点,夸大成“负有不可推卸(南明的土崩瓦解)的责任”,是欠公允的。“沉江”一折也并不存在“过分夸张”的问题,值得批判的应该是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罢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改编名作能否增删?
梁恒风交剧本时说明要参加演艺比赛、演出时长要求不超过15分钟。后来因演老马夫的演员也参加比赛,时长便要增加到18分钟。那么,大体来说,这个改编是删易增难了。
先从删说起。昆曲演出本开头,史可法内白“杀败了!”(双句)上。我以为史可法并不是败逃,他是为了到南京救主而杀出扬州的。虽然三千子弟兵全部殉国,但以救国为己任的史可法不能颓丧,他心中有未达的目的,救国任务高于一切,因此,我把内白“杀败了!”改为【新腔首板】“杀出扬州、南京直闯!”这是删,又是改。
随之而来的是增。原剧本写史可法一上场便遇上龙友、得知国破家亡的凶讯。但如果是演出《桃花扇》传奇全剧,史可法因何从扬州出走的前因观众是了解的,但现在是单折演出,必须交代史可法在什么环境中走出来、又意欲到什么地方去,于是,我就加了两段牌子、小曲。一是【困谷】牌子:
匆匆,黑夜里挥鞭河岸,
白马乏、人疲雨汗,
四野虫鸣,眼望处断壁残墙。
金瓯裂伤!
百姓遭殃!
孤臣拼忠肝,
前行岂惧路途长!
下一段小曲【扑仙令】描写他打马急奔的情境,就不细录了。
这样,就让观众了解史可法当时的社会处境和急进的目的,下面演史可法在国亡之后的境况就有了前因了。
增之二。原来预算演出是15分钟(单人参演,初稿付出之后,肇庆方来电说增加老马夫角色参演,要求增加1分钟的戏,为两个演员参演助力。这1分钟戏的任务写什么人呢?增加老马夫的戏是无疑义的。那么,写老马夫的什么呢?想来想去,一分钟戏不可能写多方面,只能写一点,写一点什么呢?应该是老马夫的核心,老马夫的核心是什么呢?从戏的内容出发,老马夫的核心应该就是他生死跟随史可法二十年(昆曲是数十年,二十年是我改的)的人生观是什么?想到这一点就好下笔了,我增加了下面一段台词:
史可法 (白)老哥呀,你跟随史某、二十年生死相随,你可有望升官?
老马夫 (摇头)
史可法 (白)你可有望发财?
老马夫 (摆手)
史可法 (白)然则你所为何来?
老马夫 (白)元帅!(英雄白)小卒一莽汉,(草野出身),国破心悲伤!元帅做榜样,生死也平常。
这样添了一笔,老马夫步三千子弟兵的后尘,先史可法殉国的思想脉络就充实了。这样写了老马夫的人生观、家国观,自然有好兵必有好帅,也从侧面衬托起史可法的英雄形象。
增之三。粤人重唱、粤剧音乐丰富。我把昆曲《桃花扇·沉江》最后一段台词扩充,填入小曲中,取得了较好效果。昆曲《桃花扇·沉江》最后的台词是这样的:
史可法 (白)史可法呀史可法,到如今满营将士都为忠魂,一门家眷,俱殉国难。叫俺孤身一人,无家可归,无国可投。这滚滚长江滚滚长江,便是俺史可法葬身之地!(唱)累死英雄,看此日江山换主,无可留恋。(白)扬子江啊扬子江,俺史可法来也!亡国罪臣!亡国罪臣!
我考虑到粤剧特色和粤剧特长,我根据上面的昆曲台词,扩写填入【萧萧斑马鸣】一曲中,并加上三句口白:
史可法 【萧萧班马鸣】天析崩,地震晃,南明半壁已沦亡。欲挽无从人惘惘,孤鸥何寄问苍茫?
天茫茫天茫茫河山板荡,数已尽数已尽难抑哀伤!三千众三千众扬州赴义,老马夫老马夫存忠气壮!(慢唱)长江滚滚浪,似热血流淌,(原速)汇进史可法,肝胆日月长!(白)长江,长江,亡国罪臣史可法来也!(沉江)
啰嗦不少了,以上是我改编《史可法沉江》遇到的不同学术观点和我对昆曲《桃花扇 · 沉江》的增删改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欢迎指正。改动是否得当,也希识者赐教。艺海无涯,鼓桨是进。